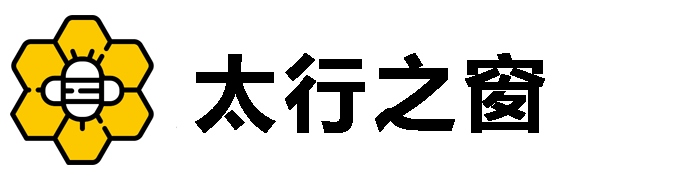克服防御性思维如果你试图避免批评请继续阅读
我和父母一起长大,他们在我八岁之前似乎很爱我,但后来莫名其妙地背叛了我。
突然,我父亲会打我,两个指关节顶在我头顶上,大喊:“你为什么不听?”
我的父母不情愿地称赞我的词汇量大、记忆力强、阅读早,所以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投入到了我的脑海中,但这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我没有真正的批准、逃避或安全。结果,我陷入了困境,总是想方设法获得他们的认可并保护自己免受他们不认可的痛苦。
后来我了解到,我正在从事“防御性思维”——依附于有利的情况,并试图避免任何可能带来批评的事情。
“但是爸爸,怎么——”,我吞了吞口水,希望他不会大喊大叫或打我。我不可避免地得不到正面的回应,我内心的批评者也会对我大喊:“你这个白痴!你为什么这样说?”
所以,在下一次之前,我会告诉评论家,“这就是我要说的”,他会回答说,“你最好希望你不要犯错,就像上次一样,你是兴奋剂!你本该是聪明的,但你是愚蠢的!”
我父亲的酗酒及其可预测的不可预测性使我的自我操纵变得毫无用处。无论我的思想多么狂热地保护我,虐待仍在继续。
在大学里,多年来我第一次体验了健康的情感生活,因为我的好朋友们接受了我是谁,而不是我想成为的人。
但是当我在1977年7月毕业回家时,在大学和研究生院之间的时间里,我从22岁倒退到了8岁。
我预料到我父亲的愤怒和侮辱,并努力坚持了三个月。
我会带着惊奇和兴奋谈论尼采和休谟,我父亲会嘲笑我,“这样的人的问题是他们做的菜不够多。”
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轻描淡写的批评,因为我在自己的头脑中投入了太多。
最糟糕的是,我知道冷笑弥补了我现在比他更高更大的事实。他再也无法够到我的头顶打我了。
但言语伤害了,那些确实如此。不可避免的结论:也许我一文不值。
我八岁时就想知道。在同一所房子里,我在二十二岁时再次想知道它。
我的头脑会拼命地保持安全,失去现在,将过去归咎于自己,并怀着恐惧的心情期待未来,以逃避虐待的尝试是徒劳的。
一天晚上,我在未经父亲同意的情况下旅行回来后,我的思绪停止了喋喋不休。也许它发生是因为我意识到我改变现状的力量是多么的微乎其微。这是我第一次记得,尽管我身处环境,但仍然感到安全。
我完全沉浸在当下。
一开始以为是抑郁症。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另一回事。
真实性。
虽然我的思绪最终恢复了喋喋不休,但我意识到,即使在最不安全的地方,我也能感受到和平的空虚。
保护
我们开始进行防御性思维,因为我们内心的批评者像监狱看守一样工作,为抵御某些外部威胁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
如果你无法解释父母的亲密背叛,你就必须在自己的行为中找到解释。心理上的选择,事件的绝对随机性,太可怕了,无法考虑。
假设我正在做我父亲最痴迷的消遣,他整整一年都在寻求准备足够的木材来为整个冬天的房子供暖。我把木头砍得很厉害;没有安全感,我会犹豫,我会摸索。我不知道如何操作工具(我会害怕它们,认为它们是他爆发性愤怒的延伸)。
多年来,父亲沮丧地从我手中抢过工具,坚持自己做事;所以我的犹豫和他的不耐烦只会变得更糟。他以为我很懒。他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但不知道他让我的环境变得同样糟糕。
也许如果我先批评自己,我想,我会避开他的批评。这种行为的悲惨之处在于它造成了终生的自虐模式。如果你经常这样做,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即使在最初的批评者去世之后,你内心的批评者也会很高兴继续下去。
我拼命地试图逃避他的消极情绪,就像一个人试图逃避波浪但没有成功。我没有轻轻地骑它或潜入它下面,而是试图跳到它上面。我知道,这种徒劳的跳跃不可避免地会被撞到坚硬的海底,无能为力。
当无法逃脱时,强加的习惯很难改掉。
我自己内心的批评者,如果有的话,比我父亲更野蛮。既然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慈爱的父亲会突然变得如此彻底,那么问题就出在我身上。
我在“防御性”喋喋不休中浪费了太多时间,尤其是在外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我会花几个小时和我的自我交谈,试图证明我喜欢的东西是合理的,比如阅读和音乐,并避免不喜欢,比如体力劳动和机械挑战,因为我知道,根据经验,这些总是会产生父亲不赞成的结果。
我是如何克服这种威胁到我每天生活的内部情况的?
1.寻求帮助。
通过治疗,我更健康的心灵成为可能。
心理健康的人有一个内在的父母,会在困难时期与内在的孩子交谈。有时,由于长期的创伤或一次性事件,那个更强大的部分,即内在的父母,变得不可用。
我找了一个搭档,他只是“站在”我更强壮的部分,直到我可以控制防御思维。我的治疗师成为了外在的滋养父母,直到我可以再次与内在的滋养父母建立联系。
对其他人来说,我一直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顾问,但我无法为自己提供同样的服务。现在我能。
2.仔细观察防御心和它的喋喋不休。
我的第一位治疗师建议我们一起工作时采用佛教方法和词汇。
突然,我发现了冥想并放慢了我的体验,以回顾我的反应性和自动思维模式。我意识到心智可以将自己与自我的虚假自我完全分离,观察并进入核心、沉默的真实性。
当时,我发现了一本救命书,琼·博里森科(JoanBorysenko)的《心灵的疗愈》(MindingtheBody,MendingtheMind)。我会开始放松,因为我读了她关于心灵如何运作、心灵是为什么而生的,以及什么不是目的的描述。
我会按照她的建议闭上眼睛,呼吸,当我的头脑变得空虚时,只是用内在的眼睛观察;最后,最重要的是,我会记得滑入“证人”的姿势,即我“喋喋不休”背后的观察者。事实上,博里森科让我明白,内在的“观察者”是滋养内在父母的最伟大的仆人。
这本书还将自我描述为具有消极保护性的“法官”,因此我开始回顾我如何调节我的思想、经验和存在。
3.接触执着和厌恶。
我后来发现的一本书,马克·爱泼斯坦的《不分崩离析》重申并进一步探索了博里森科向我介绍的东西,“依恋”和“厌恶”的动态——自我诱导的妄想和痛苦的双头怪物。
我们的自我想要“依附”外部赞美,而它想要“避免”批评。
以这种方式依赖外界的认可是不健康的,也不利于健康的人际关系。防御性思维使我们与现在隔绝并阻止我们真实地与他人打交道,因为我们专注于从他们那里获得某种反应,而不是简单地与他们互动。
此外,试图避免批评也是徒劳的,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们不能总是确定有人真的在批评我们。当我深入挖掘时,我发现,我经常将创伤引起的内心批评投射到周围人的言行中。
我将随意的谈话和行为归因于对我的更大程度的拒绝,而实际上,唯一一直拒绝和批评我的人就是我自己。
“平等心”,正如博里森科所说,是通往和平的必经之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摆脱外界的赞扬和指责。
4.重新体验内心批评者背后的痛苦。
经过几十年的治疗,非凡的坚持、努力和勇气,我终于重新体验了父亲拒绝我的错位。我和我信任的人坐在一个房间里,默默地同情和支持我,我的身体因抽泣而抽搐。
我现在可以再次回到八岁,这样我就可以重新体验创伤,同情自己,重新融入社会并继续前进。
在那些治疗课程中,我了解到我的思维是一种防御机制。这是一个脆弱的屏障,可以抵御我肠道中压倒性的疼痛,这是我几十年来无法接近的一种肯定生命但几乎无法忍受的疼痛。
突然,在重新沉浸在那个8岁孩子的世界中之后,我开发了一个内在的容器来容纳健康人的感受,这样他们就不会从情绪化的肠道疼痛中反弹到防御性思维陷阱中。
但如果不慢慢剥离防御性思维的层数,我永远无法到达那种直接而可怕的重新体验的地方。
允许自己直接体验疼痛而不试图将其合理化,这使我摆脱了内心的批评,这是创伤的非自愿产物。
我可以接受这个可怕的事实:我无法解释父亲的行为改变,这不是我的错。
我的批评者是悲惨地误用了一个绝妙的头脑,永远无法取代真实的感觉,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
免责声明:本文由用户上传,与本网站立场无关。财经信息仅供读者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X坐标y坐标是指的什么】在数学、物理、计算机图形学以及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X坐标”和“Y坐标”这样...浏览全文>>
-
【x坐标y坐标是什么意思】在数学、物理以及计算机图形学等领域中,x坐标和y坐标是描述点位置的重要概念。它们...浏览全文>>
-
【x战警中x教授叫什么】在《X战警》系列电影和漫画中,X教授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变种人(Mutant)的领...浏览全文>>
-
【x战警天启彩蛋是什么意思】在漫威电影宇宙(MCU)中,彩蛋是影片中隐藏的细节或片段,通常用于连接其他作品...浏览全文>>
-
【X战警是哪个公司】“X战警”是一部广受欢迎的超级英雄电影系列,其背后有着强大的影视公司支持。对于许多影...浏览全文>>
-
【X战警是漫威吗】“X战警是漫威吗?”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对于漫画迷和电影观众来说,了解不同超级英...浏览全文>>
-
【词语风格迥异的意思】在汉语中,“风格迥异”是一个常见的成语,用来形容不同事物之间在表现方式、特点或风...浏览全文>>
-
【词语丰腴怎么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太常见的汉字,尤其是那些字形复杂或发音不常见的词汇...浏览全文>>
-
【词语丰碑什么意思】“词语丰碑”是一个富有文学色彩的表达,常用于形容那些在语言文字方面具有高度艺术价值...浏览全文>>
-
【词语愤懑的意思】“愤懑”是一个常见于中文书面语中的词语,常用于表达一种强烈的不满、怨恨或压抑的情绪。...浏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