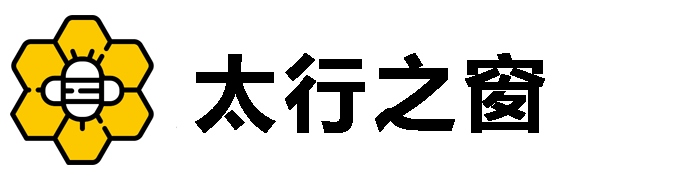最强大的治疗工具讲正确的故事
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经历了崩溃。
如果你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问我是否受到过性虐待,我会说没有。但在我30多岁的时候,奇怪而可怕的记忆开始在我的身体里浮现——连同一些故事和语言。
这些记忆片段和我对它们的反应似乎将我生活中许多不连贯的、不完整的经历粘合在一起。就好像我正在连接点并看到一个一直存在但我以前从未感知过的形状。
在某种程度上,我的阅读使我认识到我正在挖掘的创伤。我发现自己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关于暴力的文章:战争中的暴力、家庭中的暴力,以及几乎社会各个方面的暴力。我读到的几乎每一本关于暴力的书都引用了朱迪思·赫尔曼的《创伤与康复》。所以最后我把书从图书馆里拿出来了。
看这本书,感觉就像在照镜子。
我以为我度过了一个轻松无忧的童年。现在我需要重新面对那个故事并重新想象我是谁。
赫尔曼的书出版于25多年前,仍然是创伤研究的圣经:它一步一步地描绘出创伤和PTSD如何影响人们;它在公共创伤和私人创伤之间、退伍军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家庭和性虐待的幸存者之间建立了联系。
它用语言表达了许多我无法说出的经历:分离的感觉、身心之间的分离、恐惧、自责。
一开始读这本书的体验是有力量的,然后随着记忆力的增强,我开始出现惊恐发作。我感觉自己好像被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东西控制住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熬过去。
就好像巨大的痛苦和恐惧的波浪席卷我,我将失去所有的自我意识,所有的基础。我感到筋疲力尽,颠倒了。我觉得我正在失去曾经的那个人,从我旧的、沉着的、有面子的自我中溜走,进入一个被这个早期创伤所支配的新身份,被我周围的世界吓到,对人类对彼此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无法甚至想象感到安全。
我觉得地面好像在我脚下塌陷。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整理创伤故事:在我很小的时候,一名保姆对我进行了性侵犯。因为我太年轻,又因为没有其他目击者,恐惧、恐惧和羞耻感笼罩在我的身体里,周围没有清晰的语言。
但起初,随着记忆开始出现,我的记忆更多是身体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我经历了身体上的感觉和被压制、无法呼吸、身体疼痛、心理和存在恐惧的刺痛感的闪回。
我花了我所有的精力来防止我的生活崩溃。我是两个年幼孩子的妈妈,作为作家和学者,我的职业生涯相对成功。但是现在除了抚养孩子和照顾自己之外,我没有任何精力去做任何事情。
我努力集中精力展现最好的自己,为我的孩子度过每一天,满足日常需求,成为我想成为的那种妈妈——在场、倾听、富有同情心,甚至有趣。我能够(大部分)记得在他们的陪伴下如何做到这一点,和他们在一起的例行公事让我保持在正轨上,让我想起世界上的美好,尽管我很痛苦,但还是希望和爱。
但是一旦他们晚上入睡,我就沉浸在一个黑暗的斗争世界中。
我不知道我是谁了。我对自己的身体和世界的基本信任感觉受到了侵蚀。除了对性侵犯的身体记忆以及我的恐惧和恐惧之外,还有一种深深的羞耻感。
出于复杂的原因,羞耻似乎是性虐待的一种症状,比其他形式的创伤更多,尤其是当虐待发生在儿童身上时。对身体的侵犯常常会带来自责、与自我分离的感觉,以及对自我产生厌恶的感觉。
尤其是在儿童中,责备自己往往比责备应该照顾他们的成年人更容易——这是一种潜意识地创造一个更安全世界形象的方式,在那里成年人是可靠的,并且有一种控制感.
因此,当这些感觉随着所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回时,尽管我在理智上明白我没有任何过错,但我还是被一种身体上的羞耻感所压倒,从我的胃蔓延到身体的其余部分。我的身体。
因为伤口对我的影响太深了,我(不理智地)觉得它把我的每一部分都染上了颜色,好像我身上沾满了污秽。我觉得好像我小时候受到侵犯的事实在我成年后在我自己的房子里传播了污染。
当我写作时,我发现自己讲述的故事是关于创伤和恐怖、暴力和侵犯的故事。我不习惯分享这些故事。这些不是我想放到世界上的故事。我基本上搁置了我的写作生涯,不确定我是否能重新开始。
那是2009年。性虐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禁忌话题。我觉得如果我分享我的经验,我会受到不好的评价。
我个人不认识任何公开谈论童年性虐待的人。或者如果我这样做了,那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似乎不再影响他们。我当然不认识任何公开表示受到PTSD影响的人。很明显,我遭受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我不认识任何人从PTSD中康复。这是无期徒刑吗?
起初,我以为我会相对较快地度过这次崩溃,但我发现自己越陷越深。
羞愧,害怕我永远不会痊愈,我的危机是我最常隐瞒的事情。很长一段时间,除了我的丈夫、我最好的朋友以及我寻求支持的专业人士,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正在经历的事情。
我有朋友患有其他疾病,共同的朋友照顾他们的孩子,带回家做饭,整个社区都出来支持。但我没有这样的支持,所以我与PTSD斗争的秘密以自己的方式延续了我小时候经历的羞耻和沉默的循环。
一年变成了两年,然后变成了三年。作为一名作家和专业人士,我为自己设想的未来似乎永远遥不可及。
然而,渐渐地,非常缓慢地,我努力摆脱了危机。我开始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但不那么刻板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去治疗了。我加入了同样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女性团体,并练习谈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养成了强烈的冥想和瑜伽练习。
我开始打破沉默,重新编排我自己的故事,我在夜里写日记,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没有人能看到我在挣扎什么,但在那里我可以学会见证所有不同的部分。我。
将发生的事情用语言表达出来,带着同情心倾听我的身体,帮助我开始扭转局面。
当我开始只告诉我觉得最安全的少数人时,许多我不知道曾遭受过创伤的人开始向我讲述他们的创伤和治愈故事,或者朋友会让我与其他同样遭受过创伤的朋友取得联系从性虐待中痊愈。有一个完整的地下网络,人们分享故事和分享他们如何治愈的技巧。
我被我偶然听到的故事所感动,以至于我开始采访遭受各种不同类型创伤的人,以了解他们是如何度过危机的。我想为自己了解更多,人们是否以及如何度过治愈危机并走出另一边。
我与失去孩子的人、被监禁的人、患有严重癌症的人和从性虐待中康复的人交谈。我从他们的力量以及他们理解、学习和成长的能力中学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我看到这种能力使许多人利用了深刻的自我和联系的精神意识。
在我采访的人中,我看到的不是那些因创伤而破碎的人,而是坚强的人,他们非常活泼,有很多东西可以教。而我看到,那些能够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的人,也就是那些真正直面、探索和治愈的人,对他们有一种光彩。
许多人遭受了很大的痛苦,但面对那些苦难,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找到了内在和精神上的丰富来应对挑战。
听别人说,我开始远离自己的痛苦,能够从更富有同情心的见证人的空间见证我的故事。
当我看到其他人如何随着他们的生活经历而成长和深化时,我也开始重新构建我正在经历的事情。我开始更充分地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我加深了我的冥想练习,并接受了昆达里尼瑜伽老师的培训。
尽管我一直渴望继续我的生活,并认为我所经历的痛苦和动荡是有害的,并使我远离我没有做的一切(继续我的事业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发现那个时期不是崩溃,而是愈合、转变和成长的时期。
我开始明白,我之所以能够度过那段疗愈和转变的时期,是因为我足够强大,能够看到和处理我在小时候甚至年轻时都无法承受的东西。我的生活需要一定的稳定性和内在的力量,才能面对过去的挑战,让自己记住我的恐惧和困惑。
当我这样做时,我开始在自己的内心发展出新的力量和欣赏力。
常常让人感到软弱、困惑和失败的东西是通往勇气和韧性的大门。
今天我很高兴地说,我不仅治愈了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在身体和情感上都比危机前好多了。我能够以更加开放、同情和理解的方式倾听,不仅是对我自己,也是对我周围其他人的痛苦。我更能摆脱对快乐的恐惧,也就是BrenéBrown所说的不祥的快乐,全神贯注于世界的快乐和美丽。
我能够治愈是因为其他人分享了让我知道治愈是可能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相信自己有治愈的能力,并且是让我做必要的工作来度过危机的基础。他们让我看到了我的生活和心理的混乱,不仅是陷入黑暗,而且是通往更多光明的道路。
因为我知道要相信这个过程,即使当我的一部分发现很难相信隧道尽头会有光时,我仍然继续前进。
从JudithHerman的《创伤与康复》到分享他们故事的朋友,以及向提供创伤支持小组的治疗师,以及提供智慧的瑜伽和冥想老师,我得到了其他知道并相信从PTSD治愈的可能性的人的支持。
有很多次我可能会在绝望中放弃治疗,当我可能会向外看去解决我的问题,转向物质或重新投入工作,甚至寻求搬家或改变我的婚姻,而不是忍受自己内心的痛苦。
但我得到了支持,因为我知道痛苦甚至羞耻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它们不是我独有的;没有办法绕过,只能通过;当我觉得自己撞墙时,不是停下来的时候,而是寻找额外支持和更多工具的时候。
如果我们相信一种说法,告诉我们需要一直向前迈进,而感到痛苦和羞耻是软弱的表现,那么我们几乎肯定会错过治愈和成长的机会。
就像BrenéBrown将她的崩溃称为精神觉醒一样,我相信只有当我们允许自己去那些艰难、痛苦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期望我们的生活直线展开,并且如果我们不仅分享创伤发生方式的故事,还分享愈合发生的方式。
我们需要谈论治愈如何需要时间和精力;它似乎常常使我们失望,然后才能使我们振作起来;我们有时需要回去才能前进的方式;最终,如果我们坚持下去,它可以让我们更快乐、更健康、与自己和他人的联系更紧密、更有弹性。
我们需要为治疗提供安全的地方,以便它可以正常运行。我们需要给人们时间、安全和理解。
过去,癌症只是一个小声说,好像疾病本身是某种秘密和可耻的。今天,我们公开谈论癌症,但我们仍然经常低声谈论虐待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metoo运动开始改变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公开分享他们的虐待故事。
正如我们的创伤故事很强大一样,我们的治愈故事同样强大而重要。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打破沉默和禁忌,不仅围绕创伤本身,而且围绕复杂、凌乱、漫长但最终有益的创伤愈合过程。
虽然PTSD不常被提及,但据估计,有10%的女性在其一生中会患上PTSD,而且美国随时有超过500万人患有PTSD。但这些数字可能太低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深受创伤的世界,如果我们没有工具来识别它、命名它、见证它,并耐心地为愈合过程提供支持,我们就无法治愈这种创伤。
否认和羞耻是自然但不成熟的应对机制,最终会阻止愈合。打破这些模式并直视真相可能很困难;面对困难可能会导致危机和崩溃,但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经历,相信治愈的力量,我们就可以改变个人和社会。
免责声明:本文由用户上传,与本网站立场无关。财经信息仅供读者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X坐标y坐标是指的什么】在数学、物理、计算机图形学以及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X坐标”和“Y坐标”这样...浏览全文>>
-
【x坐标y坐标是什么意思】在数学、物理以及计算机图形学等领域中,x坐标和y坐标是描述点位置的重要概念。它们...浏览全文>>
-
【x战警中x教授叫什么】在《X战警》系列电影和漫画中,X教授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变种人(Mutant)的领...浏览全文>>
-
【x战警天启彩蛋是什么意思】在漫威电影宇宙(MCU)中,彩蛋是影片中隐藏的细节或片段,通常用于连接其他作品...浏览全文>>
-
【X战警是哪个公司】“X战警”是一部广受欢迎的超级英雄电影系列,其背后有着强大的影视公司支持。对于许多影...浏览全文>>
-
【X战警是漫威吗】“X战警是漫威吗?”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对于漫画迷和电影观众来说,了解不同超级英...浏览全文>>
-
【词语风格迥异的意思】在汉语中,“风格迥异”是一个常见的成语,用来形容不同事物之间在表现方式、特点或风...浏览全文>>
-
【词语丰腴怎么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太常见的汉字,尤其是那些字形复杂或发音不常见的词汇...浏览全文>>
-
【词语丰碑什么意思】“词语丰碑”是一个富有文学色彩的表达,常用于形容那些在语言文字方面具有高度艺术价值...浏览全文>>
-
【词语愤懑的意思】“愤懑”是一个常见于中文书面语中的词语,常用于表达一种强烈的不满、怨恨或压抑的情绪。...浏览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