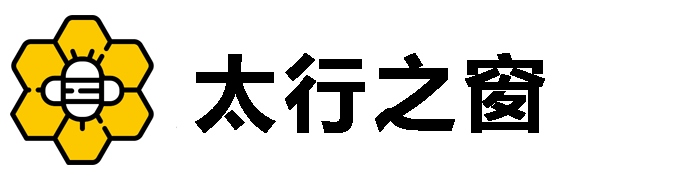我们可以克服痛苦和损失这是一个神话
我只是觉得它永远不会结束……好像我现在应该更多了,”我的朋友说,她的眼睛低头看着她的杯子。三年前,她在悲惨的环境中失去了所爱的人。
她的话让我难过,我的悲伤有很多层次:我为她的失去、她的悲伤,为她在没有这个人的情况下继续生活而每天面临的困难感到难过。此外,我对她对自己受苦的信念感到难过;仍然如此悲伤是不正常或不正常的。
这不是一个处于废墟中的女人。她过着美好的生活。她热爱的工作,美丽的家园和家庭。她是孩子们的好妈妈。但她非常难过。无论走到哪里,她都带着这种悲伤——在上班的火车上,在沙发上看Netflix的时候,出去吃晚饭。
她的悲伤是沉重的,但她带着一种掩盖其重量的优雅来承载它。这不是毁了她。然而它就在那里,就像一个心理阴影,即使在她更快乐的时候。
这次谈话让我更广泛地思考我们对失去的社会信念,我们对悲伤的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固有问题。
我的祖母在六年多前去世了。她死于脑瘤,可怕而迅速。从她确诊到她去世,只有三个星期。
她的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真实感,最初我并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悲伤。
几个月后,它开始沉入其中。正如它所做的那样,悲伤来了。它并没有消耗我清醒时的每一个想法和感觉,但它就在我身边,想让我转向它。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这很难做到。
我认为悲伤是“坏的”的文化条件在悲伤的原始体验之上添加了一个有毒的层,每次我感到悲伤时都会让我感到不知何故“错误”。
一种治愈-完美主义
“克服它。”
这些词充斥着我们周围的空间,深深植根于治愈的文化词汇中。“我已经结束了,”我们对自己说。我们向其他人保证他们也会这样做。最糟糕的是,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在某个时间段内结束它。
我们相信这是完全恢复的损失/创伤/悲伤的标志;“我现在完全没问题”的黄金标准。
有没有人完全没问题?这真的是我们的目标吗?
有没有人不带着扎根于他们存在的悲伤的根源四处走动,即使他们的幸福存在于这些深处?我不认识这些人。
我所知道的是,关于成功和幸福的最大谎言是,这些东西存在于我们没有悲伤或痛苦中。
“克服”损失的概念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理想。像许多理想一样,它很诱人,但你越接近它,你就越能看到危险。它妨碍了我们对失落和悲伤的理解,并充斥着我们内心的充实。
它使我们与我们的情感真相脱节,并让人相信我们无法实现的对悲伤过程的期望。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有一个可预测的结果:我们对我们的痛苦进行判断,并将一个自然过程变成一个病理问题,需要“修复”。
当然,在处理失去时,有时正常的情绪反应会变成需要干预的状态——如果我们最初的悲伤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而我们继续沉迷于我们的悲伤和无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治疗,也可能需要药物治疗。然而,在可以被认为是对损失的健康反应的范围内,有一个很大的范围。
对损失的正常、健康的反应是什么样的?感觉应该怎样?仍然可以体验悲伤多久?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克服它?我们应该永远吗?谁说的?为什么?“克服它”甚至是什么意思?
当我们考虑需要克服损失时,我们所指的是到达一个不可触碰、不可动摇的心理目标。到达一个我们基本上不受影响的地步,即使是我们失去的最美好的记忆,或最困难的记忆。
这是一种治疗完美主义,需要根据它的本质来命名。围绕痛苦的这种理想会导致进一步的、不必要的痛苦,并阻碍作为人类的真正意义。当我们使用“克服”损失的语言时,我们强化了一种信念,即悲伤是必须克服的。
与我们的悲伤共存
我们习惯于朝着感觉良好的事物前进,并从那些感觉不好的事物中退缩。首先,这是关于生存的。悲伤就是这样一种“糟糕”的感觉;我们退缩了。然而,这种撤回与其说是基于情绪的内在品质,不如说是基于我们对悲伤本身是不好的阴险信念。
当然,悲伤并不是一种愉快的体验——从心理学上讲,它被归类为“消极”情绪。然而,我们不是简单的生命,我们的本能也不是那么简单;因此,通常有必要违背我们的基本本能——远离快乐(如上瘾)并转向痛苦(如治愈)。
在从失去中康复的过程中,忽视和抵制我们的悲伤只会让它更深入地进入我们的心灵和身体。我们肯定知道的一件事是,当我们不承认自己的感受时,它们无论如何都会继续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以及我们在意识层面下的决策。
克服损失的想法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暗示和随后的期望,即我们的悲伤是有生命的。一个逐渐变细的时间线,在某个时间点之后,我们的悲伤量达到了一个有限的基线——零。
根据我们独特的损失和我们的个性,可接受的寿命可能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但在某些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转向我们的悲伤并问它为什么它仍然与我们同在。
我们会开始告诉自己“已经太久了”。然而,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我们都无法强迫或悲伤离开,所以我们会做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让我们的思绪远离萦绕在我们身体中的悲伤。我们会断开连接。
我们无法“修复”我们的悲伤,我们也不必
虽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可能已经描述了处理死亡的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但这些最初是为那些即将死去的人准备的,而不是为那些正在处理死亡或失去亲人的人准备的。其他。
将悲痛的线性阶段的概念应用于我们人类的失落体验的一个不幸后果是,再次期望一个有限的结局。我们经历了阶段,我们到达了终点。
不太方便的事实是悲伤是非线性的。没有任何一种模式是必须遵循的。
然而,这个有限分辨率的概念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我们的社会说话。人类特别擅长寻找解决方案。如果有问题,我们会解决它。如果有什么东西坏了,我们会修理它。
这种思维方式是让我们变得伟大的一部分;没有它,我们就不会有我们所拥有的技术进步。但是,当我们将这种思维模式应用于人类的痛苦时,问题就出现了。
我们的身体可以固定;我们可以在他们失去一条腿时给他们一条腿,缝一个深切口,用抗生素阻止感染。但是,面对失落,我们的悲伤又如何呢?我们如何“修复”它?
当我们难过时,我们并没有崩溃。我们正在受苦,这是不同的。悲伤是对失去体验的正常反应。然而,在一个痴迷于修复损坏的文化中,“克服它”的想法开始渗透到我们的原始体验中,并淡化了失去生活的启发性和悲剧美。
为我们的悲伤腾出空间
它还说明了我们对模棱两可和悖论的不适,尤其是在我们的情感领域。我们紧紧抓住各自的盒子;我们寻求“我已经结束”与“我仍在受苦”之间的明确划分。这样的门槛在生活中不存在,在爱情中也不存在。
而是两种对立、看似矛盾的情绪并存;我都很好,而且,我很痛苦。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们必须允许自己成为复杂而矛盾的存在。
治愈不是一条线,而是一波。它是有机的,蜿蜒的。它并不总是以一种能量朝一个方向移动。但最重要的是它会移动——如果我们允许的话。
当我们迷失时,我们必须学会与悲伤并存。试图将其拒之门外会将一切拒之门外。只有一条高速公路可以让身体的情绪进入心灵的意识;喜悦、悲伤、沮丧、和平——它们都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
没有替代路线。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判断我们的悲伤并将其推开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也会推开我们的喜悦。与其将我们的精力浪费在绝望地根除悲伤上,不如为它安家。一个欢迎居住的地方。
在西方,我们并不热衷于体现我们的悲伤有其自身的权利。我们无法真正控制它,就像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快乐一样。当然,我们不能围绕它来构建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创造一个空间让它共存。
它的安息之地与我们深切的喜悦和感激在同一个甜蜜点。有时我对自己说,“我的悲伤也是一个人。”这就是我的想法。在这个想法中,对它的尊重产生了。
肩并肩,悲伤和爱
我们对克服悲伤的信念也剥夺了我们最美丽的治愈机会之一——通过回忆来体验爱。
让我们保持悲伤的事情是记住我们所拥有的爱,但不能给予我们失去的人。记忆是我们重温一个人的方式。它们是我们尊重他人存在的一种方式。它们也是我们如何重新体验自己的一部分并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意义的方式。
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受苦。我们感到悲伤。这其中有一种凄美的美;这是一种有教益的痛苦,因为它源于我们爱的深处。那么,从不感到悲伤,就是一种遗忘。
当我们失去所爱的人时,我们最不想做的就是忘记他们。然而,当我们相信治愈意味着没有悲伤或痛苦时,我们会回避我们失去的人的记忆,并且在我们的回避中,我们与我们的爱脱节。因为感受这份爱,也是感受它的痛苦。
我们对不再和我们在一起的人的爱去哪里了?它住在我们里面。但要为它注入生命,我们必须让它在爱和回忆带来的痛苦旁边活在我们的心中。
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会软化。有一个释放。我们扩大。我们与自己和他人都有联系。
同情只能存在于平等之间;当我知道我的痛苦并让它对我说话时,我就能看到你的痛苦并说话。
你不需要克服你的悲伤。这不是衡量你痊愈的标准。
治愈的尺度在于你和你的悲伤之间的关系。你不必与它交朋友,但你必须学会如何让它生活在你的心中,尊重它在那里的权利,即使你尊重你希望它不在的愿望。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生活在那种二分法中是你做过的最勇敢和最大胆的事情。居住在那个空间。
让这成为衡量你痊愈的标准。
免责声明:本文由用户上传,与本网站立场无关。财经信息仅供读者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X坐标y坐标是指的什么】在数学、物理、计算机图形学以及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X坐标”和“Y坐标”这样...浏览全文>>
-
【x坐标y坐标是什么意思】在数学、物理以及计算机图形学等领域中,x坐标和y坐标是描述点位置的重要概念。它们...浏览全文>>
-
【x战警中x教授叫什么】在《X战警》系列电影和漫画中,X教授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是变种人(Mutant)的领...浏览全文>>
-
【x战警天启彩蛋是什么意思】在漫威电影宇宙(MCU)中,彩蛋是影片中隐藏的细节或片段,通常用于连接其他作品...浏览全文>>
-
【X战警是哪个公司】“X战警”是一部广受欢迎的超级英雄电影系列,其背后有着强大的影视公司支持。对于许多影...浏览全文>>
-
【X战警是漫威吗】“X战警是漫威吗?”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对于漫画迷和电影观众来说,了解不同超级英...浏览全文>>
-
【词语风格迥异的意思】在汉语中,“风格迥异”是一个常见的成语,用来形容不同事物之间在表现方式、特点或风...浏览全文>>
-
【词语丰腴怎么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不太常见的汉字,尤其是那些字形复杂或发音不常见的词汇...浏览全文>>
-
【词语丰碑什么意思】“词语丰碑”是一个富有文学色彩的表达,常用于形容那些在语言文字方面具有高度艺术价值...浏览全文>>
-
【词语愤懑的意思】“愤懑”是一个常见于中文书面语中的词语,常用于表达一种强烈的不满、怨恨或压抑的情绪。...浏览全文>>